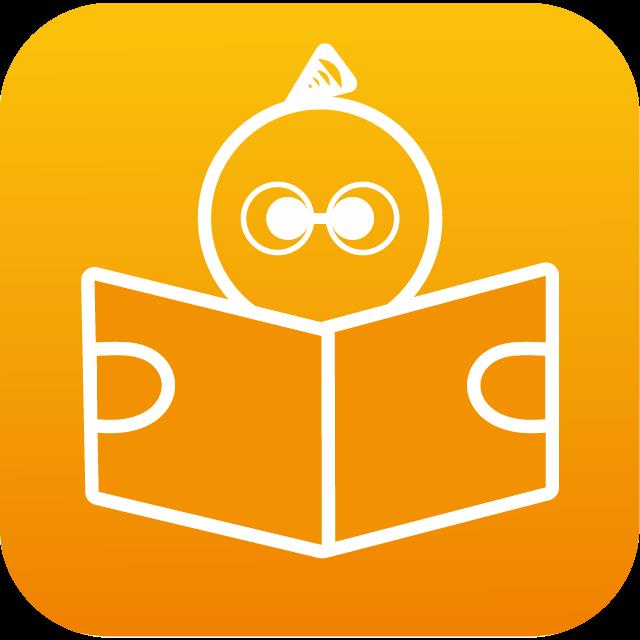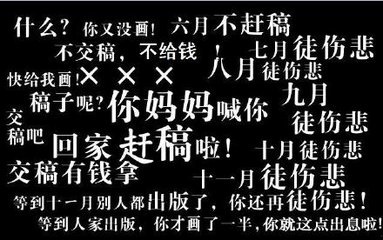
1、我很赞成通过交流研讨形式,来提高参与者的文学创作、作品鉴赏、生活审美的能力。对于参与者、观望者,都充满期待,有着无法抗拒的未知因素和谜一般诱惑。当代小小说作为民间生长的文体,几十年来正是由大众醉心于读写,以互补互动、取长补短、比学赶帮的多种形式与方法,才营造了长时期的兴旺景象。一路走来,小小说现象成为当代文坛一处亮丽风景。
2、出作品,出人才,传播正能量,永远都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方向。相比较而言,在每个人进入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为了能使自己的文学活动走的更扎实,更远些,我以为打好应有的写作基础,并学习那些有成就的名家的实践经验,来适当调整和改善自己的读写状态,减少不必要的读写误区,是一种明智的行为。
真正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发表作品上,虽然发表作品是证明我们提高水平的重要标识;还要通过系列性的学习交流,来加深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并从中认识、摸索一定的创作规律,掌握多种写作技巧和叙述表达方式,在文学的熏陶下,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品位,做一个热爱生活并能以文字与修为影响到社会环境的人,尤为重要。
3、在交流研讨中,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期待营造出一种敢于对话,乐于切磋的好风气。伯乐与千里马,应有某种专注的心意相通的气息连接。大家应该有勇气去咨询、探讨问题。因为这种零距离、面对面的碰撞所产生的每一次的收获,都会令人意外欣喜,成为某种永久的记忆。交流研讨,令人欣慰。学习不分早晚,开卷有益,切磋进益,认真安排好交流研讨、推荐佳作等流程,让每一个参与者学有所获,乘兴而来,兴浓不归。
4、过去的三十多年,小小说领域通过办刊办报、笔会研讨、征文评奖等,曾先后涌现出一批批梯次结构分明与艺术个性各异的五茬领军人物,是他们的示范表率作用,带动了风生水起的小小说读写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有效率的文学活动渐少,以致优秀的小小说创作人才匮乏。今天以网络为纽带和平台,由一些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导师们的智力资源,进行民间文学交流,为有潜质的和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提供服务,打通一条由参与者逐渐成为作者、作家的通道,以弥补小小说事业后继乏人的缺憾,其志可嘉。
5、作为小小说事业的倡导者,为业界出作品、出人才尽绵薄之力是我多年来一如既往的本份。理论话题虽然枯躁,但也是有的放矢。
我今天先谈下著名作家江岸的"黄泥湾"系列
江岸“黄泥湾”小小说系列、结构及其它
杨晓敏
江岸有十多年的小小说创作经历,他的为人为文正在影响着很多热爱小小说读写的人,尤其在山明水秀的信阳地区,正在带动出一大批文学的追随者。十多年来,江岸写出了很多好作品,有二三百篇吧,包括《黄泥湾风情》的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系列作品,像《旦角》、《寿材》、《亲吻爹娘》、《摸秋》、《开秧门》、《吃轮供》、《大风口》等等。同类题材或区域题材的系列写作,越来越为小小说作家们所青睐,取得成功者不乏其人。江岸的百多篇小小说作品,从生存背景、故事编排所虚构的叫“黄泥湾”的地方,是作者在长期的生活、观察和思考中,经过滚雪球一样的创作劳动,所立体勾勒出来的日渐丰满的艺术空间。这里有历史变迁的雪泥鸿爪,有奇人奇闻的趣味,有民俗野史的风情,可以设想,若干年后,在这个叫“黄泥湾”的艺术殿堂里,那些个鲜活的人物,男的女的,不论高矮胖瘦,喜笑怒骂,皆无拘地生长在形形色色的故事长廊里,该是何等的景象。
江岸是当代小小说领域的实力派作家,因为工作关系,他的很多稿子我曾第一时间编发,多次上了刊物头条。能有今天的创作成就,除了江岸自己的文学天赋和他的努力之外,我觉得也跟整个信阳的文学环境有很大关系。信阳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我和诗人陈有才、作家陈俊峰等文友平时聊天也多,觉得像信阳这样有着相对纯粹的文学氛围的地方还不多见。江岸能够写出“黄泥湾”这样带有地域标志的一个小小说系列,应该和身边形成的文学氛围很有关系。
对江岸系列小小说的研讨,我觉得其意义超出他个人创作的本身,也是对系列小小说怎么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哪些方面更值得我们探索,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这些创作建议,从文学层面讲,也超出了对小小说文体的研讨。事不同理同,文体不同,文学创作的理念和方法则是曲径通幽、殊途同归的。所以,无论是写长篇、中篇、散文、诗歌以及小小说的,一些创作基本原理则会心有灵犀一点通。
江岸自觉地选择了以小小说进行创作,虚拟了“黄泥湾”这样一个区域,作为他的一个心灵上的栖息地。在这一点上,这种自我选择显得十分重要。关于创作系列小小说,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也有很深的体会。譬如通过对一个地域的反复描写,或者对某个人物的不同侧面地塑造,由此不断强化读者对这一地域、这一个人物的印象,应是写小小说一个以巧补拙的有效路径之一。
江岸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天赋极高,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这使他在长期的小小说创作中,在结构故事、人物塑造、叙述节奏等把握上,都有着很好的掌控能力。他多年来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作品,《旦角》曾获2003—2004年度全国优秀作品奖,《亲吻爹娘》《吃轮供》也先后获奖,数篇作品被转载和选入多种选本。
故乡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原动力和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作家们深情回忆故乡,展开想象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作家江岸就在豫南大别山一隅的故乡故土里流连徜徉,描绘出了一幅温暖而忧伤的黄泥湾风情图。
《亲吻爹娘》是江岸的小小说代表作,也是为他赢得诸多荣誉的作品。在这篇小小说中,小三子的爹娘总是互相诉说梦里小三子亲了自己,甚至为此编瞎话自欺欺人,而当爹进城真的被小三子亲了,娘哭了,村里人却笑了,他们嘲笑小三子一个大小伙子居然亲自己的爹。当小三子回到黄泥湾,临走的时候,村里人起哄让他再亲亲爹娘,小三子半跪着亲吻自己的娘,原本想看西洋景的乡亲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甚至还有人抹起了眼泪。写亲情的小小说数量众多,《亲吻爹娘》之所以能够多次获奖、被转载,就在于角度选择新颖别致,出其不意。在乡村,我们几乎看不到父母与已成年孩子间交流爱意的表达方式,他们的爱隐忍而执着,是沉默的,羞于在语言上表达,更羞于肢体的表达。孩子年幼时,父母与孩子间的亲吻,成为思念的载体,被小三子的爹娘一遍遍回味,他们牵挂在外的孩子,只能用这样近乎原始的方式表达。乡亲们以为这样的场面是个笑话,而真的看到小三子抱着他娘佝偻的腰身的时候,他们心里却漾动着一种迟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歉疚与羡慕。
江岸在庞大的小小说作家队伍中,毫无疑问是属于实力派类型,文以载道植于心中。所谓实力派,坚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文风,在艺术追求上自觉师承传统文化,言情状物,从不投机取巧。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在外观上、细节上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注重典型化方法的运用,通过细节的真实表现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江岸文笔质朴,感情细腻,在开掘生活本质上敢于直面人生,无论褒贬,皆能明晓是非,真诚表达立场。以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乡野生活。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自己的创作倾向和人生爱憎。
譬如在《寿材》中,江岸一波三折地描写了“奶奶”的寿材的变化。寿材的变化,体现了黄泥湾人的死亡观,也是中国农村大多数老人的死亡观。到了一定年龄,他们如同“奶奶”一样,看透了生死,对死亡没有恐惧和抵触,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希望亲眼看到自己到另一个世界的住所、衣着,寿材对他们来说,就尤为重要。为“奶奶”准备好的寿材先后被大儿媳妇、小儿子、大儿子用了,她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她的寿材也越来越不成样子,到最后,只是像火柴盒子似的松木匣子。“奶奶”不让那个匣子放进她屋里,除了她不喜欢这个寿材,应该还有她再也不希望白发人送黑发人。
江岸在这里有几个细节描写:第一次柏木寿材做好,“奶奶不时地抚摩一下,那种慈爱的情形,就像抚摩她的乖乖孙儿。有时,奶奶还轻轻敲敲寿材,低沉的叩击声嘟嘟嘟地回响在棺内棺外……奶奶在别人的恭维中,总抿着嘴笑,满意得不得了”。第二次薄的柏木寿材做好,“奶奶仍然不时抚摩着,敲一敲,只不过回声没那么低沉了,梆梆梆的,像敲着一面鼓”。第三次杉木寿材做好,“奶奶再也不去摸一摸,也不再叩一叩听听响了”。第四次松木的匣子寿材做好,“往奶奶屋里抬的时候,奶奶死活不让放进去”。江岸通过几次情绪变化的细节描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触手可感的传统老人形象。
在江岸的黄泥湾系列小小说中,温暖是他努力表达的主题,比如《亲吻爹娘》《吃轮供》《大风口》《八大脚》《上门女婿》等,或者写亲情,或者写邻里情,都是温暖而美好,人性的善意在江岸的笔下得到了充分彰显,在当下这个人情寡淡、冷暖自知的复杂环境下,给我们带来的些许暖意自有其积极含义。作品以人物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因此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见其人。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了具有典型性的人物。
摸秋》同样是一篇温暖主题的作品,却弥漫着忧伤的情绪,在这种温暖和忧伤交织下,很好地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护秋队长吴孝先对支书交代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热情、积极,但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人”的一些本性,他不管妻儿老小的饥肠辘辘,甚至自己忍饥挨饿,仍要很认真地护秋,不惜抓住了自己的老婆。但当他把自己的老婆和赃物交给支书时,支书却递给他一个滚烫的红薯,告诉他自己的老婆也去摸秋了,吴孝先手里的红薯掉了。如果是现在,我们会说支书是真正的“人”,他知道饥饿,在饥饿面前他很真实。但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吴孝先的愚蠢也很真实。这就是江岸塑造人物的高明之处,他不刻意批判,不谴责,却带着理解后的同情。黄泥湾是江岸虚构的村庄,但这一方水土却寄托了江岸深厚的情感,黄泥湾里的人物都是他的亲人,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他的两眼总是饱含深情。
江岸曾在一篇随笔中说:“今生今世,能够留下一篇两篇文章,能够留下一部两部书,在百年之后,肉身烟消云散,而署有自己姓名的书籍还在人间留香,我觉得这就是今生活过的最好证明,更是活过的最大价值。”从现在看,江岸的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了,文章传世、书籍留香,相信他不仅能做到这些,而且他正在以一个作家的名义,复活着一片永恒的村庄。
冯骥才先生曾对旧天津、民国时期的那些奇人异事、三教九流情有独衷,写出了《市井奇人》系列。冯骥才写过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早期的《雕花烟斗》等非常令读者喜爱。在我看来,最能称为经典的或传世的作品,可能就是他这组《市井奇人》。那是因为他写的这些不同的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物,反映了旧天津某个层次的市井生活,无论作为文学研究,作为人物刻画,那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学经典。冯骥才的现代笔记体小小说作品,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犹如一幅幅精雕细刻的民俗画,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用“言近旨远,大义微言”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他的系列小小说《俗世奇人》,把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优势开掘得淋漓尽致。脍炙人口的《苏七块》,《巧盗》、《大回》、《刷子李》等,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往往给读者带来阅读惊喜。
比如说汪曾祺。有人说是“三篇作品”支撑起汪曾祺的文学成就,短篇(受戒)、中篇(大淖纪事)、小小说(陈小手),缺一个就不是完整的文学家汪曾祺。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大都是精短的文章,无论是他家乡的风土人情还是神话传说什么的,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才写出来的这些系列性的东西。《陈小手》是一篇让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经典佳作,小小说中塑造的陈小手这个人物形象更是小小说人物画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光彩夺目,让无数新老读者倍加青睐。对于小小说的创作,汪曾祺认为小小说应具备三要素:有蜜,即有新意;有刺,即有所讽喻;当然,还要短小精致。《陈小手》堪称汪曾祺贯彻这一创作理论的典范之作。
一方面我们要写出厚重的、长的,使我们成为有分量的作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精粹,因为珍惜读者的时间本身就是对读者的最大尊重。假如读了20万字得到一个有效信息,跟看2000字得到一个信息是一样的,所用的时间则相差甚大。当然我在说“短”的好处的时候,说到汪曾祺的时候提到这个话题,并不是说长文章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红楼梦》就很优秀,《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百年孤独》等也是代表世界级文学水准的大部头作品。我们在强调短小的精粹的,强调经济型读写的意义,强调文化内在的力量的时候,才会着意强调这一点。
再说孙方友的陈州系列,就写得很有意思。他应是一个“文化建筑学家”。一开始,我想孙方友不一定有那么明晰的追求,但是逐渐感得到一些启示,包括评论家们对他的一些提醒。他逐渐虚拟了文化意义上的陈州,在这个虚拟的地域里面,不断地塑造或者说创作着自己的人物,把不同的人物置放到这个环境里,让他们繁衍生息,时间久了,这个地方构成了一个烟火味很浓的人文景观。《陈州笔记》偏于叙事,写作背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小镇人物》重在写人,时间跨度从新中国诞生至今。前者可称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者则是底层人生的“百姓列传”。“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两个浩大的系列,不仅亮出了他最为独特的艺术名片--“笔记体小小说”,还用这一文体删繁就简的形式和见微知著的技法,构筑了发生在陈州大地上三个朝代的百年历史。
张晓林同时写着两组系列小小说:一组是“宋朝故事”,一个人物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面,有着藕断丝连的关联,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主角,在下一个人物里面则是配角,这些历史中曾经显达一时的达官贵人、以及貌似庸常的平民百姓,在张晓林笔下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渗透某些微妙的或者某种神秘色彩,从一些只鳞片爪里面,甚至传说里面,展示这些人物本质的生存状态。另一个系列叫“书法菩提”。我们知道宋代有书法四大家,苏轼、蔡襄、米芾、黄庭坚,这些人本身就有历史地位,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造诣,通过他们书法之间的脉络,从这一个渠道来探索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的端倪。
我为什么反复谈到关于系列写作这个话题?因为江岸的“黄泥湾”系列,已经取得了让大家认同的成果,也可以说在当代小小说写作者中,在广大读者里面都有一定影响。如果我们用更高的标准来期待,比如说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即把这个系列写的更加引人瞩目,我想江岸是有这个能力的。进行系列创作的时候,要有一个框架形的结构。犹如造一个大的庭院,除了各色人等,各种人物关系,也还要有雕梁画栋、楼台亭阁、花径水榭等。江岸现在写作中比较钟情的,比较偏重的就是打“亲情牌”,很感人,虽然很成功,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生活中不仅有人性美的,还有人性恶、人性丑,也有亦正亦邪的。
写小说离不开情节,要有氛围。有时候我们太注重把一个事情说清楚,往往就忽略了小说的意味,上来就直奔主题,忽略了世纪兴衰,阴晴圆缺,言情状物,留白闲笔等,因此缺少了应有的文学性。我们不能老是写晴天丽日,也可以写风狂雨骤,应给自己提出一些难度较高的创意。再说人物,我们不能老是放在我们憝悉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个地域总是从很远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我们不仅有爷爷,爷爷还有爷爷,历史的进程和很多人物命运的形成是息息相关的,像“黄泥湾”的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区域,要次第出现很多人物才行,人物之外有人物。不能就我们眼前的这几个人物,爹啊、娘啊、七大姑八大姨啊,其实还应有很多,就是要把各色人等请进来,让他跟"黄泥湾"发生联系,让他跟你的爹娘发生联系,只有啃硬骨头,作品内涵才会更丰富。今天增加几个不同的人物,明天增加几个不同的人物,一段时间以后,你的人物越来越多且与众不同,越有独特的个性和风采,那么“黄泥湾”才可以让人读了之后,感觉得到它的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人声鼎沸。小小说系列人物的塑造,通过很长时间的不间断创作,有挑战性,也有成就感。
谈点结构。我曾经有一句话被很多人引用,“人生是由无数个小小说组成的”,人生中有意义的事都是片断性呈现和间断性接续的。
像长篇《红楼梦》,可称为网状的结构,藕断丝连的结构,因为一个大观园,里面人物纷纷出场,互相发生联系,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传导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种缩影。
《三国演义》是点状的结构,貌似凌乱,但所有的点都是跟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它里面所有的点都蕴含了历史趋势和人物命运的走向,虽然很多物事没有直接关联,人物出场都很随意,甚至不考虑每一章的完整性,但是这些点拼凑出来依然是很清晰的历史画卷,太高明了。
《水浒传》是块状结构,是由众多立体故事构成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时代,课本里选了《林冲雪夜上梁山》一节,老师那天讲课好像突然来了激情,课堂上手舞足蹈,声情并茂。他说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这些故事在民间已经流传了,已经出现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人物雏形。为了写好这部奇书,施耐庵请了一个很高明的画师,把自己的想法反复讲给画师听,画师根据他讲后,画了108将的画像,挂在屋子里面。施耐庵足不出户,对画揣摹三年。直到他把某个人物的一生看透,看得呼之欲出,看108将之间的联系,将来命运是怎么样的。施耐庵在动笔之前早己胸有成竹。《水浒传》的结构简直是天造地设,仅就那些人物来说,里面哪一个人物的文字单独的挑出来,都会是一个短篇、一个中篇或一个小长篇。
《西游记》是面状结构,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不是哪一个故事比另一个故事高明,但是吴承恩太会塑造人物了,他把孙悟空一行师徒四人塑造得太好了,尽管它只是通俗文学的经典,但是依然能成为四大名著。不管你是网状的、点状的、立体的还是面状的结构,如果你没有苦心孤诣的文学经营,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定搞不起这种风景。
所以我跟江岸讲,既然我们选择了要用文学创作中的系列组合,复活“黄泥湾”这一片永恒的区域,那么就要下大工夫,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人生一辈子,只要努力,就没有干不好的事。
评论家孙新运曾写过《解读杨晓敏》一书,她概括了我不少文章观点,我把它转来与大家交流
小小说的评价标准 孙新运 谈及衡量文学的标准,其实是很难决断的,在文学理论中,人们常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对于作者的创作主旨来说,一切读者的理解和评论都不能和作者的最初意愿完全吻合,作品一旦问世,作者就应该放手,任其读者的分析理解、品读欣赏,从中可见作品评价标准的相对性。人们还说: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同、由于个人阅历不同、由于个人的好恶不同、由于个人的切入点不同,同样是分析一篇文章,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可见文学评价标准的不定性。但是,从辩证法看,文学评价从宏观上来看,还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这个标准也是相对的,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能够提出有个性,有理论依据,能够服众的文学评价标准,绝非易事。
由于文体的特殊性,小小说的评判标准和其他的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还不一样。杨晓敏说过,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即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大多数人都能创作,大多数人都能直接受益的艺术形式,这样大量的“集束式”的创作,势必会导致小小说作品数量庞大,良莠不齐,小小说评价标准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
杨晓敏从1988年始到今天,25年如一日,如夸父一样,心无旁骛执着地追求着目标,在阅遍无法计数的小小说作品后,提出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个科学定位,又提出了优秀小小说的评判标准,那就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智慧含量。这个评判标准的提出,对小小说的创作者来说,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圭臬;对小小说的读者来说,提供了借鉴赏析品味作品的必要的指导;对小小说的评论者和遴选者来说,更是一种科学的引领。
一、思想内涵 杨晓敏评价小小说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思想内涵,又继续解释为:“所谓思想内涵,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立意’,它反映着作者提出(观察)问题的角度、深度和批判意识,深刻或者平庸,一眼可判高下。” 立意是一篇作品所确立的文意。它包括全文的思想内容,作者的构思设想和写作意图及动机等,其概念的内涵要比主题宽泛得多。在文学作品中,立意的要求是:要正确、鲜明、积极向上,要集中单纯,要深刻新颖。在小小说的创作中,由于小小说特殊文体的限制(字数和篇幅),小小说的立意必须是集中单纯的,否则无法进行写作,对于小小说立意的评价正确鲜明积极向上也是最起码的要求,杨晓敏把对小小说立意的评价重点放在了深刻新颖上,又把“思想内涵”放在小小说评判标准的第一位,可见杨晓敏对此重视的程度。
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首先要看它的立意,“文贵立意”,就是文章的选材、剪材、结构、语言、表达都要以立意为依据,受立意的约束。明代的学者王夫之说过:“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率之兵谓之乌合。”立意,好比“统帅”,没有“统帅”的军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这里的“境界”是指文章鲜明的立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给香菱改诗时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从中也间接反映出曹雪芹对诗歌立意的认识,其实立意构思是判断文章高下的关键。
作为小说一种,小小说不仅要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它携带者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感悟人生、品位哲理的思想内涵。小小说在方寸之地,从一个点、一个片段、一个瞬间、一个现象入手,在短小的篇幅中,对社会、对人生进行描述和深思,对立意要求得更高。小小说的创作需要作家从小处入手,以独特的角度、适当的深度,必要的批判意识,从一件和几件小事叙述中,挖掘出现实的、人生的、人性的甚至哲理的思想内涵。这是小小说必须具备的素质和美感,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对小小说思想内涵的要求。也可以这样说,对立意的要求,是属于对小小说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诠释,是对小小说内涵的深度挖掘。在评判小小说的标准中只有充分认识了它的内涵的重要性,才能使小小说的外延得以保障,才能使小小说被读者所喜爱、所接纳、所认可,才能畅销以至于流行。
优秀的小小说无不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有着巧妙而深刻的立意。蔡楠的《水家乡》以独特的观察角度揭示小小说的深刻的立意,在小小说中蔡楠分别以“鸬鹚”、“鱼鹰”就和“老等”的角度来叙述故事阐释主题。当主人公还是鸬鹚的时候,它有朝气,有血性,是飞行力很强的野性十足的水鸟。他爱恨分明,在看到美景时,宁愿自己饿死,也不愿意打破宁静的美景,当陈瞎子捕获了他,他不顾一切地啄瞎陈瞎子的一只眼睛,并时刻准备着报复。当他为了爱情甘当鱼鹰的时候,他变得忠于爱情,顾及家庭,驯服听话,容易满足。当他失去了用自由换来的一切的时候,他也想到要回归自然,要找回野性,但是他已经失去野性,已经失去了凌空翱翔的能力,他自由孤寂落寞地变成一只长脖老等,等水来鱼来的时候,再去做一只鱼鹰。小小说向我们揭示了深刻的多层次的立意,我们可以把小小说的立意归结为环保,可以把小小说的立意归结为人生理想的放逐、追求的失落,更可以归结为人生哲理的诉求。正因为蔡楠的《水家乡》以其独特的观察角度,深刻的思辨向度,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在杨晓敏的小小说评论中,经常会看到杨晓敏对小小说作品的思想内涵的高度重视。杨晓敏在《飞翔的写作姿态——谢志强小小说印象》中评论谢志强后期的小小说时写道:“更主要的是,它靠一个深刻的立意,支撑着小小说的‘飞翔’姿态。”立意的深刻是指确立的主题不是人所共知的肤浅的道理,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出更深层的意蕴。谢志强的《黄羊泉》中的左排长因为黄羊的引路,发现了泉水,泉水甘甜无比,但是因为左排长和战士们久未沾荤腥,开枪打死了毫无戒备的黄羊,黄羊的血溅到了泉水里,从此泉水变得又苦又涩又咸。后来左排长变成了左矿长,其他人都喝从天山引来的雪水,他自己喝着又苦又涩又咸的泉水,退休了也不离开黄羊泉,并且发现远处的山就像一只黄羊。谢志强这篇小小说为读者叙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但是深刻的立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左排长枪杀黄羊,揭示了人类的贪婪、残忍和自私,揭示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世界的不正常的关系和不理智的做法,人类得到了大自然乃至世界的惩罚,左矿长用一生来承受着惩罚,但是单单一个左矿长是不能唤起人类警醒,人类的明天会是怎样呢!杨晓敏评论说:“他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华丽外表,更是丰富精深的内涵。”这种深刻的内涵奠定了谢志强在小小说界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杨晓敏在《从故事里开掘生活本质——申平小小说印象》中评论申平的小小说时说:“(申平说)现实生活中会有不同的故事,而要成为小说,则需要作家在生活中提干货、取精华,在故事这个‘庙’里,适当造出一个‘神’来。我(杨晓敏)以为作者所说的这个‘神’实际上就是文章的‘立意’。作者这几年之所以佳作迭出,能跻身于一流的小小说作家队伍,自然和不俗的创作观念有关。”立意新颖要求跳出原有的框框,以独到的视角去审视题目中所蕴涵的更深刻内容,只有从独特的角度切入,打破思维定式,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做到立意的新颖。另外创作需立意在先,构思巧妙,作品才能有创新、有变化、有奇意,这就是所谓的意存笔先,文尽意在。
二、艺术品位 杨晓敏评价小小说的第二个标准就是艺术品位,他对艺术品位解释说:“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设置故事情节,营造特定环境中,通过语言、文采、技巧的有效使用,所折射出来的创意、情怀和境界。”在《小小说是平民文学》中杨晓敏写道:“有人把小小说创作戏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可谓一语中的,小小说虽是方寸之地,却能提供无限的艺术空间。”小小说虽小,但是有很多空间让小小说作家施展艺术的才华。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小小说小,更需要小小说作家通过施展才华,提高品位,来吸引读者。在小小说的创作中,立意是第一,是基础,只有在立意深刻新颖的基础上才能谈及艺术品位,如果没有艺术品位,再好的立意只是说教。
1.人物形象的塑造 杨晓敏所说的艺术品位包括很多,首先提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三要素之一,被放在第一位,可见塑造人物形象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真正的小说关心的是人,作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帮助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而读者则通过对小说的理解领悟人生经验和智慧,对自身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了解一本小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在小说中,人物是灵魂,只有紧扣灵魂,才能驾驭文本,产生更为有效的解读。
小小说篇幅短小,塑造人物形象就尤为重要,如果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很容易会成为流水账,或者纯粹在讲故事。一提到小小说人们有时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小说中的主人公,例如人们一提到刘建超的《将军》,人们的脑海中马上会想起作品中遭遇厄运饱受磨难,处之泰然主宰人生的“哥”;一提起滕刚的《预感》,人们就会不自觉得想起那个由于相信预感而死的W君;一提到幽兰的《八爷》,人们就会想到从土地中走出来,又从容地回到土地中去的八爷,一提起王琼华的《最后一碗黄豆》,就会想起惭愧自责而又怀有希冀吃下最后“一碗黄豆”的爷爷等等。
在杨晓敏的评论中,评论小小说作品的人物形象的比例特别大,在《文坛名家的小小说写作》中评价冯骥才小小说创作时写道:“冯骥才刻画人物非常成功,其笔下人物一半是旧天津的三教九流,一半是当代生活中的人。无论写今述古,皆娓娓道来,纤毫毕现,一人一个性,无脸谱化之行,无概念化之嫌,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杨晓敏认为正是因为冯骥才对人物形象成功的塑造,才使得冯骥才的小小说富有如此高的艺术品位
在《笔会:小小说作家的摇篮》中杨晓敏评价杨小凡时写道:“他的新作《刑警李卫兵》,塑造的是铁汉柔情。亲情与职责、人性与法律、正义与邪恶,在不可回避的碰撞中,显示其大义凛然,水火不容。特别是结尾,英雄不死,豪气干云……”
小小说在方寸之间进行创作,塑造人物形象,这需要作者很高的艺术修养,所以人物形象塑造的是否成功,是衡量小小说创作的一个标准,更是提高小小说艺术品位的一个主要手段。
2. 艺术构思 提高小小说艺术品位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艺术构思。所谓艺术构思就是指艺术家在审美体验和艺术发现的基础上,按照其创作意图把对实际生活的感受与认识统一起来,酝酿、创造成为艺术形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形象思维活动。是艺术家在深入观察、思考和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加以选择、加工、提炼、组合,融汇了艺术家的想象、情感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审美意象。小说来源于生活,但它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搬,只有借助艺术构思的力量,才可能把复杂的生活素材变成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小小说创作中的艺术构思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很好的艺术构思,就会变得平淡无奇不会吸引读者,更不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冯骥才把小小说的审美规律概括为五点,其中的第二点就是巧思,他说:“不仅仅是指巧妙的结构,而且指小说中作者的思考,如何把小小说写得绝妙、好看,从中显示作家的智慧。”冯骥才先生强调了小小说创作中构思的重要性,由于小小说篇幅和字数的限制,要想像短篇小说甚至中长篇小说那样展开故事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必须合理安排好故事的叙述,详略要得当,收放要合理,显隐要得当,结尾要有启发性和开放性,要揭示谜底,要抖响包袱,要给读者留有必要的思考和发挥的空间。
杨晓敏在《笔会:小小说作家的摇篮》中评价修祥明的小小说时写道:“修祥明的小小说故事情节常有波澜,屡多曲折,富有传统小小说结构首尾照应、脉络分明、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优势和特点。”修祥明的《黑发》讲述一个能让读者流泪的故事:作者先描写了娘的俊俏和漂亮的黑发,然后介绍了人们对娘的称呼,又介绍了那个饥饿的时代,人们为了活命,就到农田里偷点能吃的东西,村里便在村口检查得特别仔细,就在这时,爹死了,大金才两岁,村里新添了许多新坟,他们都是被饿死的,而大金还是艰难地长大了。长大了的大金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把第一个月的工资30元钱交到了娘的手里,娘把钱放在地上,跪在地上对着四方叩拜,然后娘解开长长的黑发,从黑发中拿出一个已经磨损得很薄的袋子,并告诉大金,当年为了让大金长大成人,娘就是用这个小袋子偷点粮食,放在黑发中带回家的。娘告诉大金,把钱给大家送去吧,是大家养活了大金。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娘的艰辛,娘的无奈,娘的坚忍,娘的善良,让我不能自已。同时我才发现,作者在开头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娘的黑发的用意,也明白了作者用黑发做题目的良苦用心。整个故事并不复杂,但是作者构思缜密而富有起伏,伏笔的设计、包袱的抖响,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晓敏认为好的小小说应该有曲折多变,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应该有脉络清晰首尾呼应圆融的结构安排,才算得上是艺术品位上乘的小小说。杨晓敏在《秦俑和他的小小说作家网》中评价秦俑的小小说时说:“秦俑摒弃了所谓的诸多‘套路’,追寻着新颖的表达方式。他网络题材的数篇作品,结构扑朔迷离,人物,故事引人入胜,深受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青睐。”杨晓敏对秦俑小小说的构思与布局非常推崇,一方面反映了秦俑小小说创作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杨晓敏对艺术构思的强调和重视。
3. 语言的有效使用 提高小小说艺术品位还有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小小说语言的有效使用。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小说的物质媒介,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完成小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小说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小小说对于语言的要求就更高了。作者应该在千字左右,把一个故事叙述得摇曳生姿,要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要把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小小说创作中语言的重要性所在。杨晓敏在《笔会:小小说作家的摇篮》中写道:“在千把字的篇幅里,小小说的语言,是提升艺术品位的至尊法宝。因为小小说是文学入门的一条捷径,从者甚重,多有靠编排故事而乐此不疲者。殊不知,如此惰性的取巧,难以使小小说表现出多层次的内涵,容易落入通俗文化的简单审美的窠臼,致使作者长期在原地徘徊不前,归根到底,终因过不了语言这一关。” 杨晓敏把小小说的语言看得非常重,也把不重视小小说的语言可能导致的后果看得非常清楚。
在他的评论中,非常重视对小小说作者语言的评价。说杨小凡的语言“节奏明快,短促有力度”,说修祥明的语言“文笔扎实,感情色彩浓厚,能够充分调动和的阅读情绪。”说马宝山的语言“不事雕琢,自然流泻,畅顺而有节奏感。”说非花非雾的叙述“有条不紊,伏笔、照应、言情、状物娓娓道来,不疾不徐,让人身临其境之感。”说韩昌元的“语言有味,富于弹性”,说张玉玲“文字描写上柔美婉约”,说高薇“文笔细腻,尤善深入内部,捕捉人物的心理微澜。”说申永霞“语言如深涧泉水,了无杂痕;似空谷幽兰,标格卓然。”说非鱼“只有美感丛生,语言质地能表达出复杂含义的好作品,才能准确地凸现出作者赋予的寓意,才能让人在阅读中产生深层思考。”等等。在《叙述中的诗意表达——牧亳小小说印象》中杨晓敏写道:“一般说来,一篇优秀的小小说,总要在千把字的篇幅里,营造一个刺激读者阅读的‘兴奋点’,如深刻或敏感的立意、故事的陡转、人物性格的升华、结尾的悬念等。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不可忽略的叙述语言的表现力。”杨晓敏非常重视小小的艺术品位,并苦口婆心地劝诫小小说作者,一定要重视提高小小说的艺术价值,吸引读者,提高小小说的质量。杨晓敏是写诗出身的,他的小小说的语言非常凝练、简洁、丰富、新颖、深刻,为其他小小说作家提供了引领和范式。
小小说离开文学性,就只能算故事了,而文学性是由诸多艺术元素构成的
三、智慧含量 杨晓敏评价小小说的第三个标准就是智慧含量。他解释说:“属于精密判断后的‘临门一脚’,是简洁明晰的‘临床一刀’,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质量,见此一斑。”智慧是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智慧是人们生活实际的基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现代人智慧,就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所有的文学创作都需要智慧,小小说创作更需要智慧的含量。杨晓敏在《文体意识与探索精神——宗利华小小说印象》中写道:“有主流评论家曾冷静地评价中国作家,尤其是针对在尺幅之内企望图腾的小小说作家作品时说,和西方的优秀作品相比较,作品中所蕴涵的智慧量级不够,所携带的哲理性、双关语、幽默成分的使用尚有差距。”杨晓敏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小小说评价的标准中,杨晓敏就提出了智慧含量的这个标准。杨晓敏认为袁炳发的小小说《弯弯的月亮》之所以被国外教材选中,就是看中了它的智慧含量和内在的哲理。
杨晓敏所说的小小说的智慧含量主要是指小小说的结尾的处理要高明,要巧妙,要戛然而止,要有震撼力。小小说的三大特点是:立意新颖,情节曲折,结局奇特,小小说的写作由于篇幅和字数的原因,限制了小小说的厚度和广度,所以小小说创作,更重视结尾的处理,结尾处理的好坏,明显地能看出小小说的智慧含量。小小说的结尾是小小说的灵魂所在,而小小说结尾的写作技巧要体现小小说的思想内涵,要合乎小小说的艺术品位。在李永康的《小小说任重道远》中杨晓敏说:“仅就结尾而言,也是充满灵光一现的智慧产物,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妙手拈来,余味悠长。” 可见杨晓敏非常重视小小说创作中的结尾处理的智慧含量。杨晓敏特别推崇谢志强的小小说,评论谢志强的小小说是“在叙述中讲究语言的洗练,并寻找结尾的出奇制胜。
杨晓敏这样评价宗利华《越位》结尾:“在这里对人生的顿悟有哲理启示,‘双关语’的使用以及暗示中,对‘小资’们的荒唐、浅薄的讽喻,显得巧妙、善意和调侃,消解了仅限于道德层面的负重压抑感。”宗利华的这篇小小说的结尾属于补充性的,在补充叙述中,给人以哲理的阐释与启发,巧妙而不露声色。
杨晓敏是这样评价邓洪卫《同学》的结尾的:“精彩的叙述更在结尾处,作者笔锋一转,捎带着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杨修登场……真是另一个活脱脱的许攸再生。这种貌似漫不经心的结尾,在邓洪卫的其他小小说篇目中,被多次使用且常用常新,我称其为‘招牌式’的表现技法。一种不绝如缕的弦外之音,使小说弥漫出来的言外之意愈多,浸润给读者的味道则愈醇厚绵长。”邓洪卫的《同学》讲述的是许攸在呈口舌之辩、满足虚荣时无端种下祸根,结尾的杨修依然以同样的口气炫耀他的聪明,让人们对杨修的悲剧结局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邓洪卫的这种结尾可以称之为“弦外之音”式的结尾,自然而言的叙述中其实是绵里藏针,暗藏玄机。许行的《立正》的结尾也是属于这一种,看来只是自然而然的叙述,却深刻地揭示了小小说的主题并且深化了主题,让读者认识更加深刻,并且不寒而栗。
秦俑的《化妆》的结尾写陆小璐同宿舍的几个姐妹被陆小璐家人拒绝参加追悼会,在陆小璐追悼会召开的同时,她们都含着泪对着镜子化妆,她们以前是非常看不上陆小璐化妆的。这样的结尾让读者鼻子发酸眼睛发热,这种自然而然,照应开头的结尾,抒发了强烈的情感,很有感染力,也富有智慧的含量。杨晓敏评论申平的《记忆力》的结尾时说:“一个人用一辈子的努力,依然未能脱净少年时代的一记污点,着实让人对俗世喟然长叹,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袭上心头。”这样的结尾让人心生慨叹,酸楚不已。总之,纵观成功的优秀的小小说,它们的结尾或补充、或抒情、或营造意境、或照应前文、或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些小小说的成功和小小说结尾的奇特有着必然的联系,说明在小小说的创作中智慧含量的重要性。
杨晓敏在《文体意识与探索精神——宗利华小小说印象》中说道:“不久前有文友问我,故事和小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我想了想说,当然还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高下。”杨晓敏不但把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作为优秀小小说的衡量标准,简直把这些当作了区别小说与故事的基本标准。 其实杨晓敏提出的衡量小小说的标准的三个方面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是小小说飞翔的两个翅膀,两者不可偏废,同样重要,而智慧含量是使小小说展翅高飞的真正动力。好的结尾会增加小小说的内涵,提高小小说的艺术品位,更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实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即便是“精品”、“经典”、“名篇”、“力作”、“佳作”亦有其不同的涵义,何况“出精品”与“促繁荣”本身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再美妙的独奏也构不成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有了红黄蓝三原色才能调剂出色彩斑斓的油画效果。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崛起的“大众文化”,应该是真正促使人文精神升值的强心针和助推器。 譬如代表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是精英文化质地,因为曹雪芹在创作中调动了几乎所有艺术手段:深刻的内涵、曲折的故事、精密的结构、驳杂的人物以及言情状物、诗词歌赋等,注入了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阳春白雪式的文化元素,即使描绘简单的物事或对白,也在遣词造句上下足了功夫,三行读罢,即可玩味。《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大众文化质地,语言晓畅,雅俗共赏,其故事属于地道的街谈巷议,茶余饭后、道听途说的“话本”而已。每个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皆可呼之欲出。凡帝王将相、文人士子、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可以在小说中寻找到自己诠释的兴奋点。《西游记》则属通俗文化质地,稍显脸谱化概念化的描写,并没有掩盖它人物塑造丰满、想象多姿多彩、叙述妙趣横生的艺术光芒。孙悟空这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九九八十一难,难不住师徒四人西行取经,逢山开路,遇水摆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火眼金睛,屡立奇功,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每逢大难,连作者自己也写不下去了,便让悟空去纠缠玉帝或菩萨,简单地把那妖怪领走了事。然而《西游记》电视剧在屏幕上播出数十年,迄今每到学生假期,依然保持着令同行羡慕的收视率。 我们倘若仅着眼于《红楼梦》的表率性作用上,虽然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毕竟它只是“一大名著”啊。其实三种文化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处于并列关系,只要能达到极致,都会构成和占据“经典”的制高点。正因为作家们有着不同追求的写作动机和才华能量,以迥异的个性风格和艺术手段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才能创造出适合人们多层面阅读欣赏的精神产品。这本来就是一件互补互动、相得益彰的事情。
注:文章来源于网络,侵删